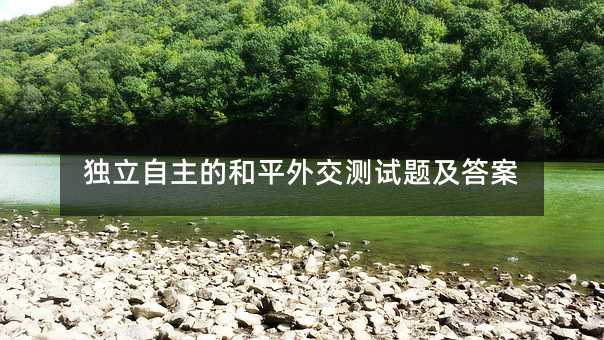“儿子一天教育我8遍,可是我非常高兴啊。”
深夜10点,闺蜜小羊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奇怪的动态。出于好奇,我私聊问她什么问题,她得意地说,自己创造了一个婴幼儿教育绝招:反教育。
以前,儿子做错了事,小羊易燃易爆炸的性格特点根本控制不住,一直叫嚣着跟他讲大道理。长此以往,小羊在儿子心中的形象就是个“泼妇”,再遇见类似的问题,儿子还会照犯不误。
有一次,他们一块过马路,还有3秒,绿灯就要转红。小羊看了看两边没车,拉起儿子的手就走,却被儿子教育了:
“是哪个平常常常跟我说,过马路宁停三分不抢一秒的?自己说过的话自己却不记得了吗?”
这件事情让小羊非常羞愧,却也因此改变了她们的亲子关系。
那之后,儿子再犯了错误,小羊会刻意压制住自己要爆发的情绪,等过个三五分钟,她会故意把儿子犯过的错误再犯一遍。譬如:脱下的袜子随意扔、躺在床上看书、吃完水果把皮都留在茶几上,等等。
儿子既然喜欢抓“小辫子”,小羊就刻意留下的这类“小辫子”给他。
果然,儿子一抓一个准。
在“反教育”母亲的过程中,儿子渐渐规范了我们的行为,领会到了“农奴翻身把歌唱”的快感,小羊也知道了换位考虑的价值。
在小羊的叙述中,我感觉到了她言语中的轻松,她再更不是之前那个抱怨连天的母亲了,而她的儿子,也在家庭中找到了我们的“地位”。
通过和小羊的聊天,我想起一个心理学名词:超限效应。
一次,美国著名作家马克·吐温去教堂听牧师演讲,刚开始,他被牧师的演讲感动得乱七八糟,恨不能立刻捐款。10分钟过去,牧师的演讲还没有结束,他听得有的厌烦,心里已经打定主意,一会少捐一些。又过了10分钟,牧师还在侃侃而谈,他决定一分也不捐了。等到牧师演讲结束,马克·吐温的厌烦已经写在了脸上,他不光一分没捐,还从盘子里偷走了一些钱。
这种刺激过度而引发的心理不耐烦和反抗现象,就叫超限效应,它在家庭教育中随处可见。
像小羊一样,在儿子犯了错误时三番五次地批评他,孩子必然会反复产生从不安到厌烦的情绪变化。
幸好,小羊找到了一个“反教育”的绝招,准时纠正了她和儿子的相处模式,不然超限效应再深入一些,就是激烈的反抗。
假如真到那个阶段再调整,就难上加难了。
十一小长假回老家,我亲眼目睹了妹妹给外甥女辅导作业的奇特方法,当时感觉新鲜,目前想起,其实也是“反教育”。
原本英语成绩不什么样的外甥女,在那段时间仿佛开了窍,记起单词来6到飞起。妹妹问她如何学的,外甥女回答,在抖音短视频上啊。
妹妹听到抖音短视频,眉头皱了皱,但她非常快就转换了情绪,问:“那你能否教教母亲啊?母亲上学的时候,最头疼的就是记单词。”
“好啊。”外甥女听母亲这么说,瞬间来了兴致,“等等,我挑几个有意思的单词啊。”
我在旁边看着这对母女互动,心里也是好奇的。
“母亲,你了解西红柿用英语如何说吗?”
“不了解,如何说?”妹妹故意装傻。
“Tomato”外甥女一遍念着,一边写了出来,“你看这个单词的架构,它是对称型的单词,中间一个ma,两边各一个to,抓住这个规律,是否就好记多了?”
“还真是哎,那如此的词汇多吗?”妹妹继续引导。
“还有不少,譬如这个单词:Tomorrow,明天的意思”,外甥女一边写着,一边给母亲讲解道,“这个词也是是对称型的单词,但它的对称是在中间,orro,前面一个Tom,后面一个w。”
在妹妹的引导下,外甥女又教给了她十几个单词,看到女儿找到了高效学习办法,她不禁感叹:“目前的手机功能真多啊,我从来不了解抖音短视频还能如此用。”
外甥女趁机得意地说:“所以嘛,你不可以一看我拿手机,就不分是非黑白地发脾气,我真的不是在玩,你相信我吗?”
“相信,将来母亲还要向你多学习。”妹妹真诚地说。
“你是做会计的,遇见不会用的Excel功能,也可以在这上面查的,我看到了好多很好的课程号,都给你关注了。”得到母亲的一定,并有机会做母亲的“小老师”,外甥女别提多开心了。
妹妹和外甥女的互动,给了我非常大的触动。
伴随手机功能的增多,它几乎成了大家成年人不可或缺的“器官”,爸爸妈妈对它越是依靠,孩子对它越是好奇,这是正常的传染。
外甥女对于手机的正确应用,让我清醒地认识到,为人爸爸妈妈,大家大可不必把手机看成会“杀死”孩子的洪水猛兽。
假如大家携带这种偏见,人为阻止孩子玩手机,是在某种程度上斩断了,孩子和这个科技年代共振的机会。
美国广播电视主持人爱德华·墨罗说:每人都是自己经验的俘虏,无人能去除偏见——只得承认它。
手机永远不可以成为“杀死”孩子的凶器,假如借助得当,它还可能是普通孩子弯道超车的利器,这个事实,大家不可以不正视,而且需要承认。
爸爸妈妈若能从孩子对手机的态度中找到他们的兴趣所在,准时引导和纠正,不少亲子关系都不会剑拔弩张。
假如,亲子关系能借由手机完成修复,爸爸妈妈在教育孩子的同时,也能同意孩子对自己偏见的“反教育”,达到一同成长的目的,何乐不为呢?
之前,重温《温州一家人》,被麦狗的成长历程第三戳痛。
小时候麦狗想出国,父亲不允许;想念书,父亲不让;想考师范,父亲不认可。父亲让麦狗辍学,到过去就读学校门口去卖鞋,受尽了同学的嘲讽。
受不了的麦狗选择离家出走,多年之后,终于打拼出了是我们的事业,开了全市最大的眼镜店,落魄的父亲去找他要钱,顺带修了一个插座,引发了一场大火,毁了麦狗所拥有些所有。
禁受不住打击的麦狗,终于将埋藏在心里的不爽怒吼了出来,说自己就是父亲手中的提线木偶。
麦狗的父亲不这么觉得,他仍然自以为是地说:“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一部辛酸史。”
这个历程,不是只专用于麦狗的,他的历程是一类人,这种类型的人在爸爸妈妈的强势教育下,离心中的自己愈加远,可能拼尽半生,也挣脱不了爸爸妈妈教育的阴影。
过度迷恋身份的权威,让不少爸爸妈妈看不见孩子的个人意愿,他们大刀阔斧地修剪着孩子的各种可能,只允许孩子奔向一种可能——他们规划的可能。
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说:“未经自省的生活没意义。”
日本作家伊坂幸太郎说 “一想到为人爸爸妈妈居然不需要经过考试,就感觉真是太可怕了。”
这两句话放到亲子关系里,是可以掷地有声的。
把它们连在一块,的意思是?
不懂在孩子“反教育”中自省和成长的爸爸妈妈,是失败的,他们的这种失败,会在若干年后“反噬”孩子,最大限度阻止孩子奔向真的的自己。
这世上最好的亲子关系,不是在爸爸妈妈高高在上的教育下形成的,而是让教育“礼尚往来”,爸爸妈妈教给孩子生活经验,孩子纠正爸爸妈妈的错误观念,这是爱意的流动,做到了,会确保亲子关系是一池活水。
办不到,亲子关系就是一潭死水。
而死水,一直都难养“活物”。